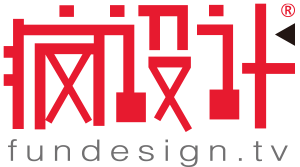上午10點,「新富町文化市場」剛開門便熱鬧非凡,外圍的東三水街市場買菜人潮絡繹不絕,館內的萬華世界下午酒場已近乎客滿。自從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接手,並經由旅德建築師林友寒的設計,這座古蹟活化而來的場館已經悄然度過8年的時間,逐漸長出了自己的樣貌。
林友寒感慨地說,「當你的作品與時間變成朋友是件非常開心的事,你看這個酒吧多成功,它充滿了生命力,還能感受到文化的原創性。」他表示,這個案子對他影響甚深,尤其是身為建築師,讓他重新思考「作者的存在是否重要」這個問題。

不存在的建築師
那並非像羅蘭巴特所提出的「作者已死」,而是作為建築師應該如何「消失」於建築之中:不以彰顯創作者自身的價值為目的,而是讓建築的價值根植於社會、文化、歷史與環境的共同體驗上。
林友寒分享道,「像我的老師拉斐爾·莫內奧(Rafael Moneo)和藝術家江賢二老師,在這方面有相似的觀點。江賢二老師一直強調『做好人,才有辦法做好藝術。』而我的老師則提出了這樣的問題:『建築是要像選美一樣,讓人覺得它很漂亮,還是要能引發人們某種共鳴和快樂?』」他認為,身而為人,讓他人感到開心還是嫉妒,正是思考的基礎出發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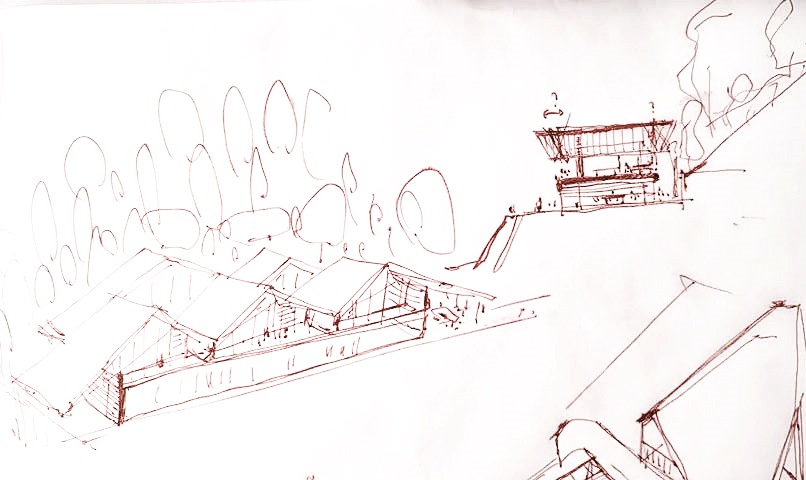
此次林友寒回到台灣,正是為了台東「江賢二藝術園區」的開園。他指出,這次與過去的案子不同,是一場與江賢二的共同創作。兩人不透過言語,而是在設計圖上彼此一筆一劃地交流。每一個設計決策,都是探索江賢二在這個場域中的筆觸習慣,以及他對世界的獨特視角,而自己則隱身在背後。林友寒笑著說:「事實上我這次選擇在這裡(新富町文化市場)與你們採訪,正是因為它與江賢二藝術園區有某種類似性。 」
對於江賢二藝術園區的設計,林友寒認為,應該以江賢二的眼睛出發,透過空間展現他的視野,特別是以他在巴黎與紐約創作時的痛苦掙扎、與音樂之間微妙而深沉的共鳴,以及定居台東後終於擁有的自由與安靜,這三段歷程作為園區設計的核心脈絡,也是林友寒試圖用建築語言所捕捉的靈魂輪廓。

為回應江賢二在創作《巴黎聖母院》時對於內心聖光的尋覓,林友寒將「光線」作為空間敘事中的主角。在展現江賢二於巴黎與紐約創作時期的區域中,光線被精心引導,以營造一種近乎神聖的感受。而當場域轉向江賢二定居台東、重拾自由的時光時,而是以更柔和、奔放的姿態,承載繽紛的色彩與自然的節奏。
以材料押韻 與自然共譜成曲
林友寒與江賢二在建築與自然關係上的理解,展現出默契。他們不希望大型的建築佔據於山頭,而是選擇將空間拆分為五個部分,順應海岸山脈的尾稜與畫作《台灣山脈》的流動之勢,像礫石般散落於地景之中。同時,江賢二創作所仰賴的光線並非直射的陽光,而是柔和的漫射光。因此,讓建築背海面山,以擁抱自然的姿態,也與藝術家對光的創作習慣形成共鳴。
在材料的選擇上,林友寒以清水混凝土搭配江賢二偏愛的耐候鋼,兩著皆是原始的材料,隨著時間與氣候的洗禮而不斷變化。特別是耐候鋼,當水氣一來便會產生緻密的棕色鏽層,「建築一定要從材料出發,那就像詩裡的文字,音樂裡的音符,材料也有它押韻的方式。」他說,清水混凝土凸顯出耐候鋼的獨特,而耐候鋼的銹色則如同土壤及樹幹,與山林相依契合。

在林友寒的建築作品中,總能見到清水混凝土的身影。「這其實有三個criteria(尺度),一來是台灣地震多,你無法避免使用較為沈穩的材料來構建建築。第二,使用清水混凝土施工時,必須有工藝投入其中,而這樣技術也延續著社會、文化的脈絡。因此,所有設計的出發點,都必須回到工藝技術。第三,清水混凝土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與初始性,它的重量感襯托出其他材質,成為建築語言中的一個押韻起始。」他解釋道。
那麼,如何選擇適切的材料與工法?林友寒認為關鍵在於觀察未來使用者的心境,思考他們將以什麼樣的情感走進這個空間。以新竹市大坪頂納骨塔「永恆之丘」為例,當時的起心動念便是希望能讓前來掃墓的人不再帶著對死亡的恐懼,而是懷著對先人的愛與敬意。因此,他選擇讓牆面微微傾斜、受光,使得每個角落都能迎接光線,沒有死角的存在。當恐懼從納骨塔裡卸載,這個場域有了隨時可以前來的可能性。

台灣先天的材料資源較少,倚賴進口,難以在追求永續採集的前提下,透過材料回溯本土文化。「不過像清水混凝土、木工技術等工法,在文化的影響下也擁有它們的特殊性。」林友寒解釋道,新富町文化市場裡的各個角落,每一塊板子、玻璃都是用雙面膠簡單黏合,輕巧、便利又耐用,並且不對原本的古蹟結構造成任何負擔,隨時可以拆卸,「這就是輕質材料有輕的做法,重質材料則有重的做法。」他笑著說。

時間的憐憫
林友寒聊建築時顯得愜意,但其言談背後所蘊含的意涵與底蘊,卻深邃無比。不過他說,自己也是到四五十歲時才真正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一位很好的建築師,「40歲以前,我以為自己有天賦,但後來才發現,那其實是一場誤會。能畫圖、創造出形,並不代表你有辦法以生命的經驗去沉澱出空間的可能。形與空間是兩回事,空間的價值往往是到了某個年紀,別人才會真正允許你去執行,你也才有能力產生某種與空間的對話。」
打造江賢二藝術園區的過程中,林友寒看見無論是江賢二還是發起人嚴長壽,都以一種憐憫的方式在回顧自己的生命,那份沉澱與共鳴無法假裝。「時間的累積,不是說會讓你看見希望,而是成為陪伴你的生命的一部分,幫助你更理解他人所走過的痛苦。去憐憫做人本身就有太多痛苦要走的過程,而非假正面強調該做什麼才對。前者是憐憫與體驗,後者則是一種指正。」

體悟,是日子、生活、經驗一次次累積而來。林友寒在設計新富町文化市場時,選擇隱藏自己的存在,因為他知道,自己不需要外界的認同,「有時候,當過於渴望他人的認同時,可能會做出像孔雀那樣張揚的事。但你也很難準確地說出,究竟是什麼讓你在某一刻放下了這種渴望。」林友寒說,當被他人定義為「好」這件事漸漸地不再重要時,真正重要的,反而是在與他者間的共鳴中找到的。
不過,他也清楚地意識到,對於是否被認同的困擾,是他那一代人的優勢。「認同的困擾,是後面世代才開始面對的。我與我的老師們創作的60年代至80年代,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幹嘛,沒有競圖,也沒有發表,就只有一小圈人知道我們的存在。」
當未來逼近
如今,科技的發展讓一切都加速,工作變得即時,AI縮短了大量整理與思考的時間,「我們戰後嬰兒潮世代已經能在生命的經驗中找到沉澱的寧靜,就像摩西分紅海一樣,我們已經有生命經驗去找到那一剎那。但對你們(年輕世代)來說,這是很不公平的。」林友寒這麼說。在剛畢業並踏上建築師的道路那段期間,他甚至還未理解「建築」的含義,只憑著自己愛畫畫,選擇了這條路,並一路摸索前行;而現今的年輕人,往往尚未畢業便被生涯選擇的壓力所追迫得無法喘息。
林友寒認為新一代建築師遭遇的「難」不只如此。30世代的建築師所面對的是地球被殘害後的樣貌,「我們這一代已經浪費了太多資源,摧殘了太多環境,而你們(年輕世代)得承擔這些後果,這是我們這一代應該感到愧疚的地方。」也因此他在教書的過程中,總著重於與環境的關係上,「我覺得重要的是,如何和下一代一同準備好,去面對現在的地球,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種種挑戰。」

40世代的建築師會直接面臨到的難,林友寒認為是創意枯乏。隨著行業的發展,能夠繼續攀升的空間越來越小,而如果走向普世化的道路,又有太多人在做相同的事情。他指出,「我覺得30、40世代的人最痛苦的,可能是兩三年內,AI就能挑戰你80%的工作量。」
他進一步解釋,建築師的工作看似高尚,但其中仍有大量重複性的工作。而台灣90%的建築師都依賴房地產,但未來多數的建案立面與形貌,業主可能會透過AI來設計。若將來業者傾向相信AI帶來的效率,不再看重創意所產生的特殊性,或者對建築師的判斷產生懷疑,那這個職業將面臨很大的挑戰與改變。
「什麼時候作者的真實性、原創性會被取代?以原創過生活的人,總覺得自己無法被取代,認為AI永遠無法超越人類的創意。不過我沒有那麼樂觀,也不願太過悲觀,我想我們終究會和AI合作,卻無法真正取代它。」林友寒道。

不過,林友寒也認為過度悲觀只會讓人感到痛苦,他更傾向去感受生活中那些值得珍惜的美好,「像在德國與台灣的創作機會很不一樣,雖然痛苦的地方都很多,不論哪國都有讓人討厭的地方,但同時也擁有它的好處。我喜歡在德國開車,高速公路的時速可以達到300公里;但我更喜歡在台灣開車,可以隨心所欲地到處亂跑。那是兩種自由,就像迪士尼經典影集《孟漢娜》的主題曲〈最美好的兩個世界〉一樣。」他笑著說,給出了令人意料之外的例子。
在藝術家的勇氣上尋找自由
林友寒觀察,德國和台灣的自卑感有某種相似之處。前者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被迫開放,過往的文化在日後的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始終被視為與「惡」相關;後者則經歷了殖民統治,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歷史傷痕,以及難以梳理文化的根源。「兩者都背負著歷史的重擔,或是持續在尋找文化裡的罪源,對我來說蠻有意思的。但那並不是說我得去歌頌它,而是它讓我有創作、立足的機會。」
限制與自由並存,要在這樣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,的確需要勇氣。林友寒說自己作為一位建築師,是依靠藝術家的勇氣來觀看社會。「建築師是沒有勇氣的,別人請我做這件事,我就只能做,我哪有說不要的這種勇氣?」他坦言,在現實中,建築師往往不會像藝術家一樣有權利拒絕某些要求,而是被現實與需求所牽引。
林友寒提到德國導演文·溫德斯(Wim Wenders)拍攝德國藝術家安塞爾姆·基弗(Anselm Kiefer)的紀錄片《安塞姆:廢墟詩篇》(Anselm – Das Rauschen der Zeit),片中其中一幅安塞姆的經典畫作〈英雄的象徵〉(Heroic Symbols),裡頭男子擺出納粹敬禮的手勢,以德國最禁忌的語彙,談論被忽略的歷史;
還有猶太裔詩人保羅·策蘭(Paul Celan),經歷父母於集中營的死亡,卻依然用德文寫詩,在傷口中選擇持續創作,那份掙扎與台灣過往日本殖民和省籍衝突有著相似的隱痛,也卡在歷史與語言的夾縫之間。文·溫德斯(Wim Wenders)從安塞爾姆·基弗(Anselm Kiefer)的勇氣中拍出電影,而他自己則在江賢二直視自身過去的凝視裡創建了園區。
「我很在乎的是,人們是否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問題,有沒有辦法體會像保羅·策蘭(Paul Celan)遇到的痛楚。能否站在他的角度,去理解那種來自於破壞自己的語言所帶來的傷。這是我在文化創作、學習環境與建築實踐中始終在乎的事。這影響我很深。」
然而,要找到那樣深刻的共鳴,實則困難。是否願意討論、是否願意換位思考、是否願意鬆動原有的價值觀,之間都藏著摩擦與不安。那就像坂本龍一在最後一次演出《坂本龍一:OPUS》中,刻意選擇了一台未經調音的鋼琴演奏,「那種變調是生命中的共鳴,走調了就是走調了。許多事情終將是我們必須接受的:走調的人、走調的社會、走調的文化。也許,這些才是我們真的要欣賞的部分。」
延伸閱讀|鳳小岳專訪|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 請允許自己呼吸
延伸閱讀|陳鎮川專訪|音樂、回憶與魔幻時刻 是他戒不掉的烏托邦
延伸閱讀|詹仁雄專訪|新一代才是娛樂的未來
撰文/麥恩 Mion
提供/臺北文創